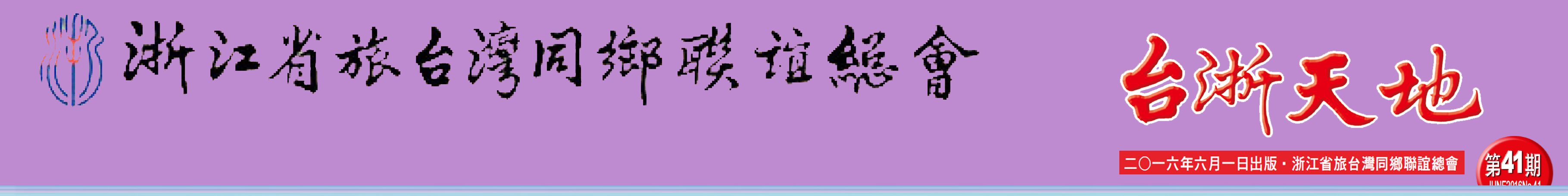|
4月4日
初春的細雨濛濛地下著。
手術後至今,快兩個月了,一直住在大姐家。
右踝關節粉碎性骨折,固定關節的石膏模子已經去掉,架著雙拐能慢慢下床活動了。腳踝已不怎麼疼,可仍腫著,整個腳面腫得鼓鼓的,內踝上的傷口由於縫合後發炎重新拆線處理,長長的彎彎的,有一指多寬,結著灰白的痂,仿佛一條寬扁的豆莢貼在那兒。腳脖僵硬,無法活動,只能勉強活動一下腳趾;由於打了五十多天的石膏模子,小腿肌肉萎縮,原本肌肉堅實的小腿肚幾乎消失了,比另一條腿細了許多。傷口處瘢痕累累,用手按著木木的,毫無感覺。整個腳面的顏色烏青。
為了消腫,大姐每晚燒盆放有中草藥的熱水讓我洗;洗了幾天後,感到輕鬆多了,便架著雙拐單腿練習行走;一開始,腳剛垂下,立刻覺得血液下湧,傷口乃至整個腳都劇烈地霍霍脹痛,腳部充血,顏色暗紅,仿佛血管就要撐破,血液要迸出似的。練習幾次後,感覺慢慢好了點兒。可腿下垂久了,傷口又腫脹疼痛得厲害起來。大姐不讓我過度活動,可一旦能下床,我便再也躺不住了。有一次,她出去了,我很想到西邊幾裏外的水庫去看看,水庫夾在兩山之間,林木蓊鬱的山麓是一所學校,我的中學時代就是在那裏度過的——那浪花閃耀的乾淨的石砌壩堤上、那映著兩岸佈滿松柏蒼翠的山峰倒影的粼粼碧波裏、那壩堤旁綠蔭匝地的茂密白楊林下涼爽的小徑上,留下多少當年我們的歡聲笑語和難忘的記憶。離家十來年了,我再也沒去過那裏,可那片粼粼波光時常都閃爍在我漂泊的思念裏,讓我魂牽夢縈。此刻我多想去那山清水秀的地方尋覓往昔的蹤跡!無法行走,我便想騎單車過去——傷腿垂著,另一隻腳蹬地,這樣總可以過去吧?誰知剛騎上車,車把一扭,失去平衡,傷腿竟如木棍般不聽使喚,重重摔在地上,鑽心的疼痛幾乎使我喘不過氣來……
我掙紮著坐起來,撫摸著自己的傷腿——這雙腿,曾騎著單車橫越世界屋脊到達珠峰腳下、曾騎著單車穿越有野獸出沒的莽莽原始森林以及寒夜翻越五千多米的大雪山,曾在最寒冷的季節以最簡單的裝備騎過世上最高最險的公路上讓人望而生畏的無數天塹的這雙腿,今天卻無法騎進近在咫尺的十多年殷切的思念裏……
雨一直下著,是那種沾衣欲濕的毛毛細雨。我架著雙拐慢慢走了出去,站在大門口,默默眺望著眼前雨霧中的田野。
門前是高楊夾道的馬路,馬路那邊就是碧綠的田野。麥田綠油油的,油菜花一片金黃;小燕子在田野上低低地飛掠著;遠處的楊樹林還沒泛綠,隔著樹林,能看見村道上有人在慢慢行走;田畔的柳樹綠了,濛濛細雨中如一團團濃濃的綠霧;水渠旁的桃花也已綻放,片片粉紅的落英順水漂流;馬路邊高大的楊樹上已掛滿了楊穗兒,有的枝頭已吐出淡紅的嫩芽,散發出濃鬱的樹脂氣息;石榴樹枝頭也冒出了火紅的針狀的嫩芽,仿佛滿樹燃燒著細細的火苗。四周鳥語啁啾,到處都是飛動的鳥影。
受傷時還是飄雪的寒冬,在床上躺了兩個月,現在已是春意盎然了。冬天在我病床上的痛苦裏悄悄溜走,春天在我病床上的思慮裏悄悄到來。
我望著故鄉寧靜的田野,思慮萬千——
從離家到現在已經十五年了!十五年前我離家時,還是一個十七、八歲對未來充滿憧憬決意去遠方尋找理想和未來的血氣方剛的青春少年,而今我帶著疲倦和受傷的身心回來了!“我曾是豪情萬丈,歸來卻空空的行囊。”這歌詞對我是多麼貼切啊!漫長的十五年,我整個兒的青春,一頭連接著快樂幸福生活的回憶,一頭連接著幻滅疲憊的無奈!難道十五年的艱苦歷程、十五年的艱辛付出,只是喚醒一場人生的迷夢?十五年裏我幾乎沒有回到這個令我時刻思念著的家鄉,只在母親病重時回來兩次,又帶著愧疚匆匆離去。沒想到今天我終於留下來了,更沒想到使我留下來的竟是一場飛來橫禍……
我架著雙拐,在門前濡濕的地面上慢慢活動著。大門左側是一片樹枝圍護的菜畦,萵苣翠綠的葉子上綴著晶瑩的雨珠兒,蒜苗長長的綠葉上佈滿了針尖般的雨點,仿佛蒙了層薄霧;菜畦旁臨著一渠流水,有幾棵敧斜的桃樹,綴滿粉紅花朵的枝條伸向水面,影落水中,凝然不動,仿佛在出神凝望自己水中的倩影。東面不遠有一戶人家,土牆青瓦,房前一棵巨柳,新綠的柳條在雨霧中絲絲弄碧,輕拂簷際。我低著頭慢慢走著,不時停下來抬頭四望,每當我的目光望向那處新柳掩映的房屋,心裏總是驀然產生一種寧靜感;那是一處老宅,雖相隔很遠,可仍能讓人感到那柳條掩映的瓦壟上佈滿青苔,那簡樸的院落裏仿佛有喔喔的雞鳴,它泰然坐落在四周新建的氣派樓房之間,一點也不自慚形穢,反而顯出一種雍容的氣度,散發一種老宅特有的靜謐。
望著它,我心裏產生一種急切想回家的感覺,回到家中那個老宅裏去。在這春暖花開的時節,一個人靜靜地坐著,坐在院子裏暖洋洋的陽光下,坐在那幾株如滿樹輕雲般盛開著花朵的杏樹下,坐在隨著微風紛紛飄落的花瓣裏和枝頭喳喳的鳥鳴聲中,坐在處處能觸景生情睹物思人的老樹舊物所喚起的對母親的懷念和對十五年前自己在那宅院裏留下的幸福快樂生活的追憶裏,用緬懷的心情去靜靜品味十多年漂泊流浪歲月裏讓我魂牽夢縈的那份老宅的溫馨與寧靜……
4月6日
回家那天,依然飄著零星小雨。
我打開鏽跡斑斑的鐵大門,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荒蕪寂靜的院落。滿院雜草叢生,圍牆下、廢棄的雞舍旁,野草深深;堂屋那兩扇我從小便熟悉的厚重的橡木門,宛然一副蒼老的面孔,帶著歲月的滄桑,面對滿院荒寂靜默著。再也看不到親人熟悉的身影,再也聽不到親切的雞鳴犬吠,再也沒有了往昔生活的氣息。
這就是珍藏著我整個兒幸福童年和無憂無慮少年的美好回憶、又使我在外漂泊的十年裏朝思暮想的那個家?
我架著雙拐,呆立在大門口,默默凝望著,心裏一陣酸楚。
一條磚鋪的甬道從大門口通向堂屋,磚縫裏生長著葉片深綠的車前草和開著黃花的蒲公英。我順著甬道慢慢走向堂屋,心怦怦跳了起來,好像只要推開那兩扇門,等待我的依然是離家前溫馨的情形。
隨著安放在石臼內門軸沉重的吱吱聲,空虛的屋內如同撲面噓出一口冷氣,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天陰沉沉的,屋內光線昏暗。我的目光首先落在了正牆上方那塊長長的鐫著“花開富貴瑞氣呈祥”的匾額上;這古色古香的匾額,同我的記憶一樣長,那時每逢節日,母親總是用雞毛撣子拂去上面的灰塵,晚上,匾額下麵的方桌上紅燭高照,閃耀的燭光照著桌上豐盛的佳餚和滿屋歡樂喜慶。牆壁上的壁畫落滿了塵埃——這些畫是我離家後張掛上去的,它們對我是陌生的,然而有的壁畫一角脫落了,露出下麵更陳舊的、我離家前就已張貼在那兒、我曾無數次欣賞過的熟悉的畫面——那些與之有關的過去幸福生活的回憶立刻在腦海裏復蘇了,仿佛那讓人懷念的過去時光就凝聚在這些畫面上,保存在每一件舊物裏,只要目光觸及,立刻便釋放出來;我輕輕揭開上面的那些畫紙,久久注視著,時間仿佛在迅速倒退,退回到十年前那讓我在外漂泊流浪時魂牽夢縈的歲月裏去……
堂屋三間,每間都有牆壁隔開。當年,中間是客廳,東間是母親的臥室,西間是我的臥室;每間都有小門相通。我拄著拐杖在每個房間裏來回慢慢走著、看著,內心如屋裏的空氣般空虛黯淡。母親不在了,這個屋子的靈魂也消逝了,房間裏死氣沉沉。我不禁有點詫異:這個屋頂,這四堵牆壁,就是我孩提時的庇護所,珍藏著我整個童年的幸福和快樂?記憶裏如水晶宮殿般的地方,就是這個空落落的房間?
母親睡了一輩子的木床已經搬了出去,那裏留下一片空白;我的目光停留在那裏,記憶在那片空白處填寫著思念。那張古舊的黑漆桌子也在,桌子的下端雕刻著鏤空的古色古香的花紋——這張桌子每一個細小的部分我都非常熟悉,抽屜上安裝著黃銅製作的鼻兒,鼻兒上掛著近似長方形的黃銅片,這是開關抽屜的把手,也是我童年的玩具:記得孩提哭鬧時,母親便用手指敲那黃銅片,發出清脆的叮叮聲,以後我便不厭其煩地去敲它以取樂——這是我童年最早的記憶;以後上學了,只有桌子那麼高,晚上便和姐姐一起趴在桌子上學寫字;外面房間裏放著紡車,母親晚上總是坐在紡車前紡線,每晚我都是在嚶嚶的紡車聲中安然入眠;那時的冬天似乎特別冷,夜特別黑,屋裏也就特別明亮溫暖……
我的眼光四處搜尋著,想尋找任何一點能喚起對母親回憶的痕跡……
我走向西間,這是離家前我的臥室。這裏的一切與我離家時都不一樣了,與母親的臥室相比,這裏真是判若兩樣!牆上掛著色彩鮮豔的壁畫,頂棚整齊乾淨,窗前掛著淡綠色印有松鶴圖樣的窗簾——這一切都是我離家後母親佈置的。
母親,雖然我離家十五年,雖然這個房間空了十五年,可十五年裏,你依然把它收拾得乾乾淨淨,時刻盼望著那個不知下落的小兒子會突然歸來!母親,你就是在這時時刻刻的期盼之中,在這望穿雙眼的思念之中,度過了漫長的十五年啊!你生活中的一切都融在了這盼望等待裏了!我打開衣櫃,櫃子裏整整齊齊疊放著幾條嶄新的緞面被子,這是母親在我離家後用自己種的棉花一針一線為我縫製的;而你,母親,至死都蓋著那兩條粗布棉被!當你為那個多年沒有音信不知是死是活的小兒子執著地縫製棉被的時侯,母親,你心裏在想什麼呢?
這就是母親啊!我心裏又一陣酸楚……
自母親去世的兩年裏,老屋已沒人居住了。可許多傢俱還以原來的樣子擺放著。我長時間地在老屋的三間屋子裏走動著,那些細物遺跡,無不勾起我對母親的思念,無不讓我想起母親在時的情景。
老屋的地面是夯實的泥土,沒有打水泥地板,也沒鋪磚。我坐在門口,突然看見地面上有幾道明顯的劃痕。我的心驀地一動,那是母親留下的。記憶裏,每年秋末冬初,母親總在堂屋地面上鋪張席子,坐在席子上為家人做棉衣棉被。初冬偏南的太陽從門口斜斜照進屋裏,落在母親身上,也落在地面上。母親做針線累了,停下手中的活兒,抬頭看看太陽,又低頭看看落在地面上的日影,便用針在日影照到的地方劃道痕跡做標記;久而久之,母親能從照進屋裏的日影上,看出各個節氣和每日的時辰。
陰雨天氣裏,母親總靠近門口坐在此刻我正坐的地方,用簸箕簸去糧食裏的秕糠。那個簸箕還在,此刻就放在我對面那口當年用來盛糧食而今空空如也的羅缸上;簸箕的邊緣已經破損,用白帆布包裹著,並用針線密密地縫在那裏——那是母親勤勞的雙手長年累月把簸箕磨破,又親手把帆布縫補上去的。我默默地凝視著簸箕,也許那是母親生前最後一次使用後,把它放在缸上的;它像一隻碩大的貝殼,靜靜地擺放在那裏,仿佛正等待著母親那雙手再次去動用似的……
瞻顧遺跡,宛然在昨,可母親卻永遠離開了這座她生活了一輩子和寄託著畢生心願的老屋,永遠不再動用那些她使用了一輩子的傢俱。有時我外面進來,推開那兩扇我從小就熟悉而今依然原樣的沉重的橡木門,聽著從小便聽慣了的門軸轉動時發出的吱吱聲,恍惚覺得一切都沒有改變,一切都和以前一樣,只要我走進屋去叫一聲母親,便會看見母親那熟悉親切的身影……
4月11日
回來時,老宅院子裏的那三棵杏樹已是花褪殘紅青杏小,綠蔭滿地子滿枝了。
杏樹不大,只有手腕粗細,彎彎的黑裏透紅的樹幹一米多處,枝杈便縱橫交錯著向四周伸展了。嫩綠的心形小葉片剛在枝頭舒展,葉片間結滿了豆粒般大的小小青杏,乾枯的殘花還裹在小杏上,胎衣一般。杏樹雖小,枝杈很密,結的果實更稠,每根枝條上都綴滿了,真比葉子還稠許多,雖才豆粒般大,枝頭已是沉甸甸的了。三棵杏樹相隔四、五米遠,呈三角形,樹枝在頭頂交錯在一起,分不出彼此來;當枝繁葉茂時,這裏一定是一個綠色的天然帳篷,樹下一定是一片涼爽宜人的濃蔭。
樹下有個粗大的半尺高的樹墩,那是一棵幾十年樹齡的老榆樹,鋸倒後留下的,如小圓桌面一般。我把樹墩四周的荒草枯枝清理一番,把新發的小榆樹苗剷除掉,搬個小竹椅坐在樹下,把受傷的腳抬起來放在樹墩上,以免長時間下垂,血向下湧,引得傷口更加腫脹。
滿院都是野草。四周牆腳下,稠密的小米蒿緣著牆壁瘋長;老樹根部都生出了幼苗;通往堂屋的磚鋪甬道上,磚縫裏也長出了許多葉片深綠的車前草和開著黃花的蒲公英。黑色和白色的蝴蝶,在花草間無聲地飛舞著。昔日圍著歡聲笑語和幸福快樂的四周高高的圍牆,如今卻佈滿了青苔,只圍著一院荒涼和寂寞。春天的陽光暖暖地照著,雨後初霽的野草綠得發亮,太陽下散發著濃鬱的香氣。偶爾從鄰家隱隱傳來幾聲喔喔的雞鳴。
我默默地坐著,目光在院子裏搜尋著記憶中的痕跡。那時,窗前有一棵杏梅樹,一團綠蔭罩著窗戶,我總愛坐在屋裏,透過窗櫺,透過那團綠蔭向外眺望——當時我並不知道,就在這眺望之中,渴望遠方憧憬未來的願望在心裏潛滋暗長。左邊是幾棵刺槐樹,春天槐花開發,滿院清香,常有幾只鸛鳥落在雪白的花叢裏引頸鳴叫;夏天,我們在樹幹上捆綁木棍搭天棚,晚上便睡在天棚上,透過枝影看星星、看月亮。大門旁有一棵大桐樹,樹下是個斜坡,冬天下雪時,我們晚上在雪上潑水,第二天早晨結了冰,便在那裏溜冰玩耍……
記憶非常奇特,有時幾十年你都沒想過的細小的事情,卻會在?那間清晰地浮現出來。當我的目光在院子裏巡視,許多從沒想過的往事生動呈現,宛然眼前。比如,當我看著當年大桐樹生長的地方,突然便想起童年的一個冬天,雪下得很大,半尺多厚,我們在堂屋和廚房之間打掃出一條通道;近中午,雲層中微微露出了日影,母親從堂屋出來,向廚房走去時,那棵大桐樹上的一隻喜鵲突然嘎嘎叫了起來;母親站在甬道上,舉起一隻手放在眼前以擋日光,抬頭望著枝頭的喜鵲,自言自語:“喜鵲叫,客來到,下這麼大的雪,誰會來呢?”母親並不一定相信鵲叫客來的說法,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但那天中午,姨媽帶著表哥表妹真的踏雪而來。也許是那天中午飯桌上的熱鬧氣氛,也許是那次巧合的事以後經常提起,這件事才沒有在記憶裏徹底湮滅。現在回想起來,我仿佛又看見那白皚皚的雪地,雪地上枝頭站著喜鵲的那棵大桐樹,母親站在門前的甬道上,在微茫的日光雪影裏,用手遮擋著日影向上眺望著……
我靜靜地坐著,默默觀望著眼前這座累年在外漂泊的歲月裏給我美好的回憶、如今卻荒涼冷落的老屋老宅,荒蕪的庭院裏處處彌漫著一種引人遐思的溫情;它依然是我漂泊得疲倦的心靈的棲息地,我這麼急切地回到這裏,不就是想在這處處能喚起幸福回憶的老宅氛圍裏,緬懷它業已飄逝的靈魂——母親,為自己渴盼的心情尋找慰藉?
那些記憶中的大樹大都不存在了,只有屋後的那棵大榆樹還在。
它是村中最高最粗的大樹。站在村外,遠遠便望見它龐大的樹冠,如綠色地標蔚然挺立於村莊上空;坐在院子裏看去,無數如虯龍般的黑色枝柯,從老屋後面高聳半空,在屋頂上空縱橫交錯,織成一個遮天蔽日的巨大“翠蓋”,遮住了北面半個天空。雖然還沒生葉,可稠密的榆錢已使滿樹翠綠一片。
十五年前我離家時它就是這個樣子,十多年過去了,它依然枝繁葉茂,陰翳蔽日。十餘年的光陰改變了老宅的一切,唯有它,似乎超然於時間之外,一別經年依然如故。當我對著它默然凝望,仿佛面對著一個久別重逢的故人,帶來許多過去的回憶。
父親對這棵大樹的感情帶點迷信色彩。曾有人高價要收購它,父親執意不肯;甚至有人提起,父親就會怒形於色。在他心裏,這棵大樹成了鎮宅之寶,只要它挺立著,它龐大的樹冠就會蔭庇這座老屋,也會庇佑這個家庭的運阼,這處老宅的活力就不會消失,能挺過任何風雨災難,重新繁榮起來!
我理解父親的心情,在這個院子裏生活了一輩子,老宅中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融入他的血液,成為他生命裏難以割捨的一部分;懷著執著的心願操勞了一生,誰知到了該享天倫之樂的耄耋之年,老境與老宅一樣突然變得如此孤單淒涼;他不相信這個寄託著他畢生心願的地方會如此敗落下去,也不相信他畢生渴求的東西到頭來竟會是個泡影,雖然到了垂暮之年,內心也在苦苦掙紮著,期盼著一種能給老宅和夙願帶來轉機的事情如奇跡般降臨。屋後這棵大榆樹,便成了他這種精神的寄託——每當他懷著空虛寂寞的心情走進這個院落,抬頭看見那覆蓋著屋頂的龐大樹冠,渴望老宅如大樹般茁壯下去的心情便不會泯滅!
4月15日
回來好幾天了。
院子裏三棵小杏樹的嫩葉一天天舒展開來,顏色由嫩綠轉為深綠,樹蔭更濃了。微風吹來,綠葉搖擺,發出輕柔的沙沙聲;風在柔嫩的綠葉間似乎也變得溫柔了。青杏兒一天天長大,蒙著一層細密的銀色絨毛。天氣一天比一天熱,涼爽的樹蔭更顯得可愛了。坐在樹下,陽光透過枝葉斑斑點點灑落下來。杏樹低矮,站起身,頭便伸進了枝葉間,稠密的青杏碰著口鼻;當杏兒成熟時,滿樹黃澄澄的果實,張口便能含在嘴裏。
狀如小喇叭般的紫色桐花開放了,刺槐吐出了嫩芽兒,椿樹冒出了火紅的嫩葉兒。屋後那棵老榆樹,榆錢變白,開始飄落,滿樹嫩葉生了出來。各種鳥兒聚集在大榆樹的綠蔭裏,從天亮到天黑,一整天都鳴叫不已:麻雀的啾啾聲、喜鵲的嘎嘎聲、斑鳩的咕咕聲、楝雀的噓噓聲、黃鶯高亢婉轉的歌唱聲,都在那片龐大的綠影中響起。
大榆樹是鳥的天堂。清晨,曙光乍現,只聽屋後大榆樹上一樹鳥鳴,竟無半秒間歇,聲勢如此浩大,仿佛每一片葉子都在盡情歡呼;隨著天光大亮,鳥兒紛紛從枝葉間飛出,飛落在四面八方的田野和綠樹叢中,仿佛滿樹葉片被風陣陣吹飛。傍晚它們飛回來的時候,簡直是一種奇觀——暮色中已顯得黑暗的龐大樹冠,高聳在充滿絢麗晚霞的天空背景上,鳥兒們在天空急遽飛著,倏忽便鑽進去不見了,仿佛大榆樹具有奇異的磁性,從四面八方吸引著天空中的飛鳥兒。
當我看著白天從大榆樹裏絡繹不絕地飛出覓食、傍晚又接連不斷落進去過夜的鳥群,不禁暗想:這棵大樹上到底聚集著多少鳥兒呀?
開始,我還以為鳥兒只要飛進大榆樹稠密的枝葉裏,便看不見影兒了。其實不然。
午後,我面朝北坐在院子裏的小杏樹下,正對著屋後那棵大榆樹。有一隻鳥兒,在榆樹的綠蔭裏好像吹號子似的不停地叫著,叫聲音節複雜,抑揚頓挫;它不停地叫著,總是重複著同一個音調,好像誰尖著嗓門在重複呼喊著同一句話。我抬起頭,想看看是什麼鳥兒。
這時,天空陰暗,大榆樹龐大的樹冠映著灰白的雲層,透出斑斑點點的天光,仿佛是在陰暗天空的背景上,鏤空雕刻的一副巨大的墨綠色的屏風。燦爛的陽光下,大榆樹是一團濃得化不開的綠影,滿樹都是閃光的葉片;沒有陽光,反而看得更清晰了。我在枝葉漏出的縫隙裏看見一隻抖動的鳥影,接著是第二隻、第三只……當我仔細辨認,好傢夥,我看見滿樹的鳥影——大榆樹的綠葉不停地抖動著,開始我還以為是微風在吹拂,原來竟是一樹的鳥兒在飛舞、在追逐嬉戲、在啄著綠葉和榆錢。其情形,宛然一個巨大的綠色蜂巢,聚滿了蠕動著的蜂群。 我用力拍了拍手,想看看滿樹鳥兒轟然飛起的壯觀場景。然而,我的手拍疼了,大樹上的鳥兒卻毫不為所動,依然悠閒自在地在枝葉間追逐嬉戲著;反而別的樹上的鳥兒被掌聲驚動,倉皇飛起,迅速飛進大榆樹的懷抱裏去了。我真為老宅中的這棵大樹感到自豪!它是鳥兒們的棲息之所,它用繁茂的枝葉為鳥兒們遮風擋雨;它挺立在老屋的上空,空中的飛鳥便有了安全的歸宿;當鳥兒們在別處受到危險和驚嚇,便飛入它的懷裏尋找安慰,它以母親般博大的胸懷容納它們、庇護它們!
呵,故鄉!你不就像那棵吮吸著你泥土中的養分長大的大榆樹嗎?而我,不正是一隻在外受了驚嚇、倉惶飛入你懷裏尋找慰藉的小鳥?
4月16日
這幾天,鄉親們聽說我受了傷,回來了,常來這座很久沒人走動的老宅裏坐一會兒,說一些安慰話,言談舉止中透著親切質樸的鄉情。
天晴的時候,我便坐在小杏樹下的樹蔭裏。杏樹的綠葉完全舒展開來,層層疊疊交織在頭頂,陽光很難再透過枝葉照射下來;陽光灑在綠葉上,從下麵看,如片片晶瑩透明的碧玉,濾下一層迷人的綠光。青杏長得很快,十天前我回來時,還小如豆粒,轉眼便長大了,沉甸甸的把枝條壓得更低,即使坐在矮椅上,也觸手可及。
這三棵小杏樹下麵,便成了我“會客”的地方。
來人的時候,從屋裏搬出幾把小竹椅,圍坐在樹蔭下,樹墩上放一盒香煙;問候話,關心話,天南地北隨意暢談。我不但知道了一些治療創傷的偏方,也知道了許多發生在村子裏的新聞舊聞。清風吹來,枝影扶疏,頭頂綠葉沙沙作響,鳥雀在枝頭喳喳鳴叫,老宅寧靜的空氣裏充滿了春天花草的芬芳。
鄉親們大都信命,相信人生禍福都是前定。因此,他們能夠坦然地面對生活中的各種變故,保持一種柔韌寬鬆的心境。他們也說出這樣的話來勸解我:
“好事壞事不是一成不變的。有些事,看起來是好事,也許會變成壞事;有些事,看起來是壞事,說不定會變成好事。就拿你受傷這事來說,也許正因為你傷了腳,不能再出去了,會有一件想不到的好事落到你身上;要是你沒受傷,出去了,這件好事就不會再讓你遇上……”
這並不是說我受了傷就是件好事,也並非是說我會因此得到什麼實在的好處;他們只是拿這種禍福倚伏的道理告訴我:事情既然已經出現,就無法挽回,心情要想開一些,放寬一些,換個角度去看待那些不如意的事情。的確,陽光下的物體,只要有承受陽光的一面,必有背對陽光的陰影,只看你站在什麼角度去看待了。
其實,在外漂泊了這麼多年,能在這美好的春天裏,坐在十多年來日夜思念的故鄉涼爽宜人的綠蔭下,靜靜地感受處處散發著溫馨回憶的老宅的這份寧靜,對我長久渴慕的心靈來說,這本身就是一種無法估量的補償。
有時,我獨自坐著,看著搖曳的樹影,聽著滿耳鳥鳴,那些在外漂泊時思念家鄉的情景便栩栩如生地浮現在眼前。記得我騎單車在雲貴高原上漫遊的時候,一天傍晚,我在荒野裏看見了一棵刺槐樹,正是暮春時節,樹上開滿了白色的槐花;那時,我已好久沒見過這種樹了,在我心裏,這是一種故鄉的樹——我離家時,故鄉的山野和家家戶戶的院子裏,都生長著這種粗大的刺槐樹,春天槐花開放,滿山遍野都是雪白的槐花。當時我看到那棵開花的刺槐樹,仿佛看見了故鄉春天的美景,格外親切,我趕過去,撫摸著它粗糙的樹幹,望著枝頭串串下垂的槐花,沉浸在對故鄉的思念之中,直到暮色降臨,天空飄起了晚霞,我還留戀在樹下彌漫著的思鄉氣氛裏,久久不忍離去……
今天,能有機會坐在故鄉春天的樹蔭下,坐在漂泊在外時的殷切思念裏,這難道不是一種幸福嗎?
4月17日
今天,我小學時的一位老師——申寶玉先生來了。
刮起了風。樹大招風,的確,當小樹新綠的葉子呼啦啦搖擺的時候,屋後那棵大榆樹已嗚嗚作響了。風在不同的樹上發出不同的聲響,這與樹枝的軟硬、葉片的質地、樹木的大小有關。風梳理著柔長的柳條,發出的聲音也輕柔;楊樹滿樹都是清脆響亮的喧嘩,這聲音符合它帶點兒硬度的葉片;杏樹的葉子較楊樹薄了點兒,發出的聲音也較軟。耳朵聽慣了,但聽風聲便能辨出樹木的種類。那棵大榆樹則與眾不同,它發出的聲響與枝葉無關,那是一種低沉的嗚嗚聲,雖不響亮,卻氣勢磅礡,讓人感到一種深沉的力度。
風在大榆樹龐大的樹冠上嗚嗚地響著,吹得滿樹幹枯發白的榆莢漫天飛舞,如雪片般紛紛飄落在屋頂瓦壟上和院子裏。我坐在小杏樹下,正觀望著這暮春時節難得一見的滿院“雪景”,一轉頭,吃了一驚,只見申寶玉先生抱著兩箱禮品從大門口走了進來。
我急忙拿起雙拐,想站起來迎接。他已快步走上前,扶住我的胳膊讓坐下,自己也在我對面坐了下來。
呵,老師,您怎麼知道我受了傷?又怎麼想起來看望一個您二十多年前的學生?
我望著他那雙深陷的睿智的眼睛,那張熟悉親切的面孔,當年母校的情景突然間便清晰地浮現在眼前:我仿佛又看見了當年楊柳掩映的那個校園、那幾排教室、教室前面那面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校園外綠草鑲邊的操場、操場旁蛙聲陣陣的池塘;我仿佛又聽到了掛在辦公室門前那口鐵鐘的當當聲、教室內琅琅的讀書聲、講臺上不倦的教誨聲、以及課間十分鐘校園內快樂的歡笑聲……
他用那只拿了幾十年教鞭和粉筆的手,在我還沒痊癒的傷口旁輕輕撫摸著查看一番,關切地問起了事故發生的緣由。
那真像是一場噩夢——
春節期間,一位朋友約我去他家。十多年沒見面了,他又約了幾個昔日好友,聊得很盡興,各自談論著十多年前彼此留給對方的印象,和記憶裏一些難忘的事情。告別時,朋友把我送到門前的馬路上。那天很冷,刮著寒風,我把鴨絨襖上的帽子戴在頭上,系緊帽帶,回頭向朋友揮揮手,騎著摩托車便離開了……
事後目擊者說,當時我騎著摩托車由西向東行駛,速度很快;一輛銀白色的麵包車由東向西開過來。在一個丁字路口,麵包車突然向南急轉,我躲閃不及,一頭撞了上去;巨大的撞擊聲把附近的幾戶居民都驚動跑出來觀看。撞得很厲害,麵包車前的保險杠嚴重變形,而摩托車的碎片如砸碎的玻璃一樣散落一地……
我醒來的時候,正坐在行駛的車裏。當時肯定是垂著頭,因為我首先看見自己胸前殷紅的血跡;朦朧的意識裏,我恍惚覺得像是很久以前在看一幕恐怖血腥的影片。我怎麼會成了影片中的主角了呢?思緒在模糊的意識裏掙紮著:這不是真的,我肯定是在做夢,就像以前許多次從夢中醒來,睜開眼睛,夢境還沒完全褪去一樣;等我徹底清醒了,眼前的一切都會消失,這只不過是一場噩夢在剛剛睡醒的意識裏的殘餘,那時就會發現自己正平安無事地躺在床上。遮掩意識的暈眩如霧紗般逐漸退去,我突然感到有點兒不對勁兒,身旁坐著兩個人正攙扶著我,其中一個女人不停地用衛生紙在我頭上擦拭著。我這才明白出事了。
我急忙扭頭向車窗外看去,我看見了剛剛離開的那位朋友家的紅色大門,原來車又開回來了。我讓車停下,下車去敲朋友家的門。那個女人要攙扶我,我頗為輕鬆地說不用。我當時並不知自己哪兒受了傷,也感覺不到疼痛,只是走路一瘸一拐的。朋友後來說,他打門一看,大吃一驚,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剛把我送走,關上門回到屋裏,就這麼一會兒功夫,再開門時,眼前卻站著一個血人,臉上的血還在不停地往下流。這前後不超過十分鐘!
朋友急忙把我攙扶上車,送進醫院。臉上多處擦傷,鼻樑骨折,左眼上方縫合五針;右踝內側粉碎性骨折,需動手術——醫生脫下我的鞋子時,裏面竟滿是鮮血……
事後,我怎麼也想不起當時的情形。不但車禍發生的地點,相撞時可怕的場景記不起來,就連從朋友家出來,到車禍發生前這段記憶也消失了。我能記起的事發前最後的印象,就是自己騎上摩托車,轉身向朋友揮了揮手;而朋友家離那個丁子路口有一裏路遠——從離開朋友到再次敲他家的門,這十來分鐘內發生的事情,完全在記憶裏失落,沒有一點印象……
(未完待續)
(綠 野)
|